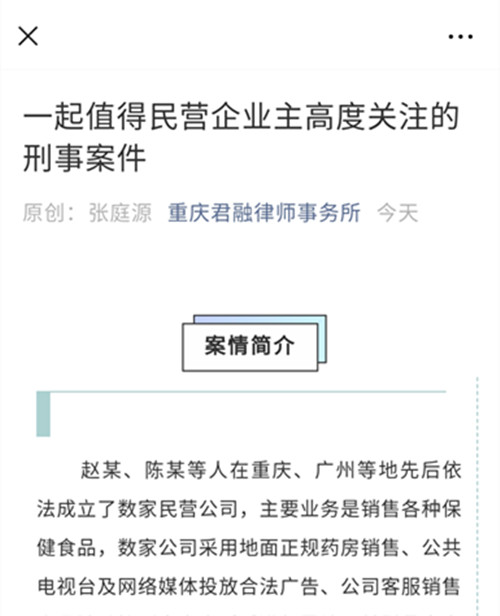|
赵某、陈某等人在重庆、广州等地先后依法成立了数家民营公司,主要业务是销售各种保健食品,数家公司采用地面正规药房销售、公共电视台及网络媒体投放合法广告、公司客服销售人员被动接到客户电话后进行回访、并引导客户进行购买的商业模式开展经营业务。公司销售的保健产品也是有国家批准文号、合格证明的正规产品,是通过向有资质的正规厂商购买的,在产品包装上的说明书、功效等内容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销售时,公司未在产品包装上作更改,顾客在购买时可以明确看到产品上经行政机关审批的功效说明,公司的销售价格也是在合理加价范围之内,顾客在收货时也有权选择退货退款,若不拒收就此完成合法产品的买卖交易。公司所有的经营环节基本都是合法正常的,问题出现在公司销售人员与客户电话沟通时,部分销售人员为提高业绩,在销售部分保健品时,为增强顾客的信任感,有冒充身份(专家、教授、医生、调理师等)的行为,或者是采用夸大保健品功效等方法引导客户购买保健品。法院一审判决认定公司为诈骗犯罪集团,公司所有销售金额全部被认定为诈骗犯罪金额,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销售经理、销售小组长、普通销售人员等近百人被认定为诈骗犯罪集团成员,均以诈骗罪论处,分别被判处不等的有期徒刑和罚金。 该案多名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现已提起上诉。本案暴露的一些问题值得中国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主高度关注及讨论。 诈骗罪与民事欺诈 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为犯罪构成必要要件的,行为人出于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设置圈套的方法等欺诈手段,使对方陷入错误认识,从而骗取他人财物。以买卖产品为幌子实施诈骗的犯罪行为,从行为人的身份开始到行为人所捏造的事实等系列环节上来看,基本都是彻头彻尾的虚假,毫无真实性可言,买卖双方之间根本不存在产品交易和交付,行为人是一种实质性欺骗,非法占有目的明显。 而民事欺诈虽有骗的行为,但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目的,行为人用夸大事实或虚构部分事实的方法,诱使对方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以此谋取一定的利益,此种“虚张声势”的欺骗方法,其本质是为了获得或促成交易的资格和机会。 而本案涉公司在经营机构的设立、公司日常管理、销售产品的购进、对外的广告投放、产品的交付、退款退货的处理、依法纳税、接受行政机关监管等一系列方面都是公开、合法的,没有任何秘密和隐瞒。在案涉公司的整个经营链条中,仅有部分销售人员,在部分产品的推销介绍上,在部分的时间对部分的购买者实施了冒充身份、诱导顾客,购买的行为,但现在以以偏概全、一刀切的方式推定案涉公司全部人员由上至下均实施了该行为,是没有根据的。销售人员在销售保健品过程中虽带有销售欺诈性质,具有隐瞒真相、夸大事实的违规行为,但销售人员隐瞒真相的目的不是为了骗取财物,而是为了尽快、成功地将保健品卖出,完成产品的交易。因此,对此类案件可以通过民事法律途径进行解决,对违规行为可以通过行政机关进行行政处罚。 是否为犯罪集团 作为一个公司,其组织性本身是存在的,但是不能把公司正常的组织性等同于犯罪集团从事犯罪的组织性。公司每个销售组的销售方式不是一样的,销售人员在销售时采用的方式方法也是随机应变的,有些销售人员采用了对产品进行介绍的话术模板,但销售话术模板也只是销售人员的一种专业化营销技能的体现,案涉的话术模板的内容基本上是产品的成分、厂家、功能等介绍,还包括一些中医药的基本知识,不能说采用了销售话术模板就有违法问题。且部分员工的行为不能代表公司整体性行为,在有充分证据证明属于部分行为的情况下不应想当然地推定为全员行为和公司行为,从而上升到犯罪集团的高度。 本案也无任何证据证明案涉公司的管理层人员(如股东、经理、销售部长、销售组长)有组织、策划、指挥销售人员采用冒充身份、虚构事实的方法进行销售,公诉机关的公诉人在法庭上也明确说明本案的特点是自下而上的蔓延,是管理层默许的结果,且不说公诉人的这个蔓延指控没有证据证明,即便如此,也不能认定是犯罪集团。 对犯罪数额的认定问题 法院依据“办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确因被害人人数众多等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逐一收集被害人陈述的,可以结合已收集的被害人陈述,以及经查证属实的银行账户交易记录、第三方支付结算账户交易记录、通话记录、电子数据等证据,综合认定被害人人数及诈骗资金数额等犯罪事实”这一规定,而将公司全部销售额认定为犯罪数额。 在案情复杂、涉案人数多的情况下,“综合认定”不是给办案人员机械、麻木地推定犯罪数额以借口和理由,司法是理性、专业的,不说要做到完全地无懈可击,至少也要基本合符逻辑判定。在公司运营中有正常合法的营业收入,也有部分违法所得的情况下,怎能简单粗暴地就将销售额认定为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从而成为犯罪数额,成为其量刑依据呢。需要指出的是,公司数年来销售金额高达数千万元,全部被认定为诈骗金额,而报案的金额仅仅只有区区的数十万,且这些报案数额中还有相当的一部分是不主动、不自愿的,是公安人员的引导下完成的所谓诈骗报案材料。 根据最高检发布的指导性司法文件:对于确因客观原因无法查实全部被害人,尽管有证据证明该账户系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且犯罪嫌疑人无法说明款项合法来源的,也不能简单将账户内的款项全部推定为“犯罪数额”。要根据在案其他证据,认定犯罪集团是否有其他收入来源,“违法所得”有无其他可能性。如果证据足以证实“违法所得”的排他性,则可以将“违法所得”均认定为犯罪数额。 社会影响 企业在宣传、销售自己产品时为引诱客户购买产品、提高交易的机会,虚构、编造一些不实信息或夸大功效因而收到工商管理机关的行政处罚,但这些企业在受到行政处罚后仍能正常经营,有些企业甚至被多次违法警告也没有受到刑事处罚。如鸿茅药酒事件展示出来,该企业因为不当宣传曾经多次被行政处罚,但这家企业在内蒙当地从未受到司法机关的刑事责任追究,甚至被当作地方名片、明星企业,该公司负责人多次入选内蒙古年度十大经济人物。 还有被公广为诟病的“莆田系”医院,使用各种花里胡哨的词汇和噱头包装出“治病良方”,以博眼球和制造噱头的方式进行广而告之,实际的医疗水平却弄虚作假、差强人意,以致于屡屡造成患者病情加重不说甚至倾家荡产的情况,这类医院却鲜有受到行政处罚,更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 为何本案案涉企业,仅仅是在销售部分产品的宣传上部分公司员工出了问题,公司就被认定为诈骗犯罪集团,所有工作人员被按诈骗定罪,其严厉的刑事处罚结果让人难以感受到公平的存在。 审理诈骗案件应当重点从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健康发展与保护交易安全出发,在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罪刑法定原则以及刑法谦抑性精神的前提下,准确有力地打击诈骗犯罪。若没有妥善处理好刑民交叉案件,厘清经济纠纷与犯罪的界限,以刑事手段插手企业经营活动,将会给企业增加无谓的刑事风险,对民营经济造成巨大的打击,严重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而民营企业家将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中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甚至万劫不复,我们的刑法不是调整一切社会矛盾的法律,司法机关也不是处理一切社会矛盾的机关。 结语 企业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或服务,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不顾法律及行业规定,铤而走险,对其产品进行夸大宣传,这种做法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这种利用广告虚假宣传的欺诈手段的行为方式的是有可罚性的,但不属于财产类犯罪的诈骗罪,诈骗罪需要有非法占有为目的,且数额较大的财产转移、占有作为犯罪成立的前提条件。在买卖合同关系中,本案案涉企业作为销售方,在众多公开的系列经营环节上均是合法的,仅仅在产品介绍这一个片段环节不诚信,存在虚假宣传的行为,应当以虚假广告行为论处为宜,不应不符事实的拔高放大,更不应该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将全部销售额认定为犯罪数额,本案存在此罪与彼罪的区别,也存在刑事和行政处罚的考量,希望二审人民法院能有一个更合理、更公正的判决。 原创:张庭源 重庆君融律师事务所 |
更多精彩新闻请点击:http://www.peoplessjj.com/《时事经济观察》